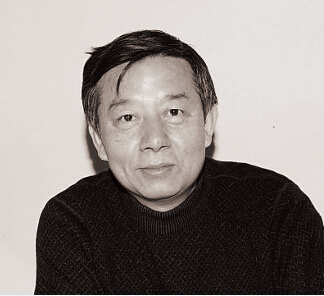
藏族是中華民族大(dà)家(jiā)庭重要的一員,高(gāo)原風光無限。藏民生(shēng)活,高(gāo)原風情,深深吸引着一代代藝術(shù)家(jiā)的關注,自來(lái)是中國繪畫(huà)最具魅力的題材庫。但(dàn)幾十年來(lái)将高(gāo)原生(shēng)活視(shì)為(wèi)自己的生(shēng)活、将高(gāo)原題材作(zuò)為(wèi)藝術(shù)表現的唯一題材的藝術(shù)家(jiā)不多(duō),吳長江卻是獨特的一個(gè)。從上(shàng)世紀80年代初趨今三十餘年,他不間(jiān)斷地深入高(gāo)原,記錄高(gāo)原變遷,采撷藏民生(shēng)活,寫照高(gāo)原民族的心魄。遼闊高(gāo)原是他藝術(shù)表現的不變的舞台,高(gāo)原的魂魄是他不懈的藝術(shù)跋涉的遠方。80年代早期,他以懷斯一般的迷蒙與傷感,表現高(gāo)原陌生(shēng)而神秘的遠山(shān)。之後,他不斷地用畫(huà)筆帶着我們一次次走進高(gāo)原風情,走進藏民生(shēng)活。這一次,他用三十年來(lái)的藝術(shù)積累,把我們帶入藏民的豐饒家(jiā)園,直面衆多(duō)原樸的形象和(hé)神情。
在衆多(duō)繪畫(huà)藏民題材的熱潮中,也出現了兩種弊端:一、将藏鄉生(shēng)活視(shì)為(wèi)一種風情奇觀,聚焦于奇異的表象。這是一種奇觀化的傾向。二、鍾情于民俗學的原樸現象,把弄化石那(nà)般賞玩高(gāo)原的原始與冷漠。這是一種化石化的傾向。前者失于表象,後者則失于冰冷,兩者都将高(gāo)原生(shēng)活視(shì)作(zuò)與己無關的他者。吳長江的繪畫(huà)沒有(yǒu)這些(xiē)弊病,在他的作(zuò)品中灌注着一種激情,一種對于高(gāo)原人(rén)的凝視(shì)和(hé)關懷。面對面的寫生(shēng),在寫生(shēng)中直面人(rén)的生(shēng)機生(shēng)趣。這是一種樸實而真摯的交流和(hé)關懷,是通(tōng)過彼此的對視(shì)來(lái)激活的、主客體(tǐ)融合為(wèi)一的轉釋和(hé)表達。這裏邊蘊藏着人(rén)的存在,其中既有(yǒu)對象的生(shēng)動存在,又有(yǒu)此時(shí)此刻的主體(tǐ)存在。從這個(gè)意義上(shàng)講,高(gāo)原之魂不僅是遠方的他者之魂,更是延伸到我們生(shēng)活中、感動和(hé)勾聯着我們全體(tǐ)的共在之魂。
長江繪畫(huà)的材料與方法是素描水(shuǐ)彩,樸素而生(shēng)動。這種方法有(yǒu)三方面的特點。
第一,把握形的能力。長江善于在抓形的同時(shí)抓神。這種捕捉帶着力量,帶着速度。如若火(huǒ)栗在手,必須趁熱熟剝,不得(de)有(yǒu)須臾滞怠。人(rén)物的形神,無以切分,隻在描畫(huà)之間(jiān)一同帶出。長江手勢沉重,總是一層層地刻劃,剖膚剔骨,倍顯沉郁厚重。
其次是獨特的塑造方法,這是一種寫的方法。筆在不間(jiān)斷的運行(xíng)中滑動,帶出光暈一般的結構,并将感情投入其中。這種渲染和(hé)構寫是有(yǒu)感情的,飽含受藏民的神情驅使而激活出來(lái)的生(shēng)命體(tǐ)驗。在這感情和(hé)體(tǐ)驗的深處,有(yǒu)一種共同的存在被镌刻在那(nà)裏。長江自己的某種性靈被誘發出來(lái),那(nà)種共同的如高(gāo)原般堅毅沉穩的神情在天地人(rén)的交彙中得(de)以開(kāi)啓。
第三是樸真的色彩。長江的色彩調性迥異于西方光色冷暖的系統,有(yǒu)一份東方礦物色素的純樸魅力。那(nà)藏民的面龐滿含着曆經風霜的濃厚。中國人(rén)曆來(lái)講究去華麗(lì)、求素美。長江的水(shuǐ)彩正若古錦素壁,有(yǒu)一種滄桑,又有(yǒu)一種洗不去的素彩,一種內(nèi)美的特質。
長江以三十多(duō)年不懈的高(gāo)原激情,以突出的把握形的能力、獨特的塑造方法、樸真的色彩,為(wèi)我們帶來(lái)這個(gè)生(shēng)動的高(gāo)原人(rén)物的長廊,真切地塑造出樸實而感人(rén)的高(gāo)原之魂。這高(gāo)原之魂堅毅、感人(rén),向着所有(yǒu)的人(rén)們發出邀約和(hé)召喚。
中國美術(shù)學院院長許江
本站(zhàn)總訪問量: 地址:南京市江東北路220号 郵箱:jsszghxh@163.com
 金盞花(huā)微信平台,歡迎加入!
金盞花(huā)微信平台,歡迎加入! 金泓文化微信平台,歡迎加入!
金泓文化微信平台,歡迎加入! 吉林省中國畫學會微信平台,歡迎加入!
吉林省中國畫學會微信平台,歡迎加入!